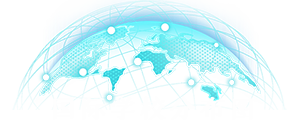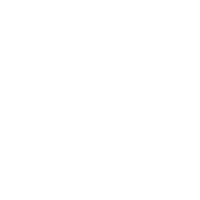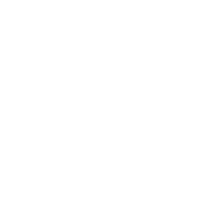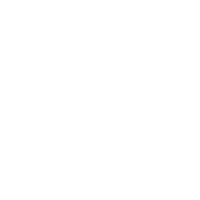國際學校和傳統教育的沖突
時間:2016-11-07 13:41 國際學校網
昂貴的選擇
一次見Funny,是在北京星光天地的一間咖啡廳。生于上世紀50年代的她,看起來和同年齡的人很不一樣,穿一件牛角扣大衣,呢子及膝褲,寬大的紅色雞心領毛衣里面,是紅色的法蘭絨格子襯衣,言談舉止充滿同齡人少見的活力和自信。她大學讀的專業是西方音樂,曾經專門去法蘭克福學習古典音樂,還是北京市吉他協會的會員。如今則是一名身兼數職的自由職業者,既教授鋼琴、西班牙古典吉他,也從事心理咨詢工作,有時候還幫人做形象設計。她說自己求學和工作都是在“非常西化”的環境里,這讓她在自己所屬的年代里,做出了很多與環境有著極大反差的決定,其中看起來背離常規的是她選擇的育兒道路。
“兒子很小的時候,我就去燕莎的外國玩具專柜給他挑玩具。”。她買得多的是在“玩具舶來品”中享有盛譽的樂高。這是一種類似積木的拼接式玩具,但樂高通過在塑料的配件表面制作出各種凹凸形狀,大大提升了玩具的黏合度和成型功能。依靠工業技術對積木小小的功能革新,玩具商在商業社會將它開發到極致——樂高系列的用戶從幾個月延展到幾十歲,嬰兒和老人都是它的消費對象。上世紀90年代初,Funny的孩子才三個月時,Funny就推著到他到燕莎的進口玩具專柜選購樂高。當時燕莎還是北京少有的高檔西方商品消費場所,玩具專柜前擠滿了前來觀看,卻又很難下決心購買的中國父母。一套進口玩具動輒好幾百元,對當年一個普通的中國家庭來說,很少會給孩子玩具預算如此高的金額——這不僅是消費能力問題,更是“孩子成長更需要什么”的觀念問題。在“買一套昂貴但讓孩子得到快樂”的玩具與“買一套昂貴但讓孩子學到知識的課程”之間,大部分中國家長只會對后者掏出錢包。
但Funny不這樣選擇。她有一個在當時看來頗為離經叛道的理念:對孩子來說,學習知識不重要,快樂才重要。“人生會有很多挫折,很多意想不到的磨難,我希望孩子長大后是一個幸福感指數很高的人,即便未來只掙很少的錢,或者遇到很大的打擊和困難,但他的嘴角還能有一絲微笑。”Funny用一個藝術工作者的浪漫來描述她認為孩子成長需要的能力——抗打擊能力。她認為成年后關鍵時刻的處變不驚,來自于一個人小時候感受快樂的多少。“我研究過心理學,在16歲之前,孩子的心靈需要得到絕對的保護。在這之前所有的挫折和傷害,都會給孩子的內心留下傷痕,這種傷害是不可逆的。”
玩具是Funny用來給予孩子快樂的一種方式。他們家并不算非常寬裕,丈夫是工程師,Funny的自由職業能讓她獲得很大程度的身心自由,卻不能提供非常豐厚的收入。但這個家庭在樂高玩具上的累積支出達到39萬元,家里的配件多得足夠開一間樂高游戲室。因為是上世紀90年代樂高在中國少有的忠實用戶,Funny和兒子還上過《中國日報》的英文版。
玩具并不是Funny為孩子做的昂貴的支出,只是她漫長育兒道路的一個隱喻:這位生于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媽媽,篤信西式的育兒方式和產品,并不計代價地實踐并堅持她所認定的方式。她不僅為孩子選擇了昂貴的樂高玩具,還選擇了臺灣人辦的幼兒園,英國人辦的國際學校。隨著孩子成長,這條西式教育之路的代價也越來越昂貴。近20年前,國際學校在北京還是個新鮮名詞,僅有少量為外籍在華工作人員開設的學校,并不是中國家庭可選擇的教育產品。Funny孩子入讀的國際學校完全按英國的學制、教學方式和收費標準,一學年分為三個學期,每學期學費5萬多元,一年的學費接近18萬元。在上世紀90年代初,鮮有中國家庭愿意負擔這么昂貴的費用,去購買一種與國內公立學校迥然不同的教學方式,入學時Funny的孩子是學校里唯一的中國學生。
選擇什么樣的教育,不僅事關個人喜好,更是一種與代際相連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Funny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想要為孩子提供一種與傳統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她因此跳入了一個巨大的阻力漩渦。初的阻力來自家庭內部。“為了減輕孩子從幼兒園進入小學時的不適應,學校規定一年級可以陪讀一段時間。我媽媽退休前是老師,還曾經被評為北京市較優教師,因此覺得自己很懂教育。她去陪讀了一個星期,回來后極力反對孩子繼續在那里上學。她說國際學校什么都不教,就是讓孩子玩。”昂貴的學費則是另一層壓力——Funny的家庭生活一度非常拮據,甚至曾因為學費問題將孩子轉學到英國一年,再從英國回到中國公立學校的國際部就讀。求學之路頗多動蕩,但Funny從沒動搖讓孩子遠離傳統教育的決心。
傳統教育之弊
Funny對傳統教育的排斥一部分來自個體感受。她回憶自己的上學經歷,將傳統學校的教育評價為“老師不懂得愛,除了發號施令就是指責”,孩子在教師威權的壓抑下,得不到尊重,也因此喪失自信和快樂。
直到2014年,就讀于國內公立學校的孩子依然有著和Funny相似的感受。12歲的女孩陳欽怡今年剛從國內一家公立學校轉到了一所國際學校。陳欽怡講了一個讓她印象深刻的事情:“在公立學校的時候,有一次我負責做板報,原來的做法都是把板報內容打印后貼出來,因為我學過畫畫,覺得打印的字沒有藝術字好看,而且在電腦上做很費時間,于是就準備了一個手寫的藝術字版本,但老師堅決不同意我的想法,說一定要按原來的做法打印,這樣顯得更整齊。”用美術字還是用打印版,看起來是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情,但對一個孩子來說卻包含著若干個具有突破性的選擇:是不是要打破辦板報的常規?怎么樣實現自己的新想法?敢不敢說服老師接受自己的想法?成長就是由無數個這樣微小的選擇累積而成的。在自主選擇并獲得認可的過程中,孩子慢慢建立起自尊和自信。但以老師威權為核心的傳統教育在大部分時候剝奪了孩子自我選擇的權利。雖然陳欽怡已經畫好了藝術字,但老師還是堅持按原來的方式,將板報做成打印版。陳欽怡沒有做什么爭辯就順從了老師的決定。“我想還是不要跟老師爭吵,不然他會生氣,會說‘你別浪費我們的時間’。”這個12歲的小女孩靦腆、禮貌,即便在談話中模仿老師發怒提高音量的語氣,也是緩慢安靜的神態,但能感覺到被迫放棄自己想法后隱忍的挫敗感。她的平靜中包含著一種小孩子的無奈:“我也沒有辦法,老師總是對的嘛。”
陳欽怡曾入讀的公立學校是一所北京市學校,不少名人之后也在此就讀。對很多選擇傳統道路的家長來說,無論從硬件還是軟件衡量,這所學校都是讓人羨慕的教育起點。但孩子的評價標準卻迥異于成人,他們看到的學校和成人社會中口口相傳的學校頗有不同。“學校的硬件設施是很好,甚至比我現在就讀的國際學校的設施還多,但大多數時候都不開放。”陳欽怡說。她很喜歡學校走廊里陳設的一些科學感應裝置,比如伸手過去就會亮的燈,或者一有外界力量進入就會徐徐展開的荷花……但如果不是有領導或者來賓參觀,這些勾起她好奇心的有趣裝置,只是走廊里死氣沉沉的擺設,既不發光也不會動。在孩子的眼里,老師的素質也不太夠得上“為人師表”,“他們在辦公室里穿著拖鞋,有的老師還把腳蹺在桌子上,好像辦公室就是他們自己撒野的一個地方”。在公立學校里,陳欽怡喜歡一位教授實驗課的老師,但喜歡的原因并不是從這位老師那里獲得了多少知識,而是因為得到過一次情感上的支持。“有一次學校舉辦種植比賽,我們小組按照老師教的方法操作了,但種子發芽后又死了。我們覺得實驗失敗了,都很沮喪。但后來老師調查發現種子是壞的,他給我們道歉,后還獎勵了我們。”對孩子來說,有太多看起來微不足道的挫折需要成人世界的理解和鼓勵。陳欽怡對這位實驗課老師的評價是“善解人意,能聽進去我們的感受”,但“這樣的老師很少”。
這些看起來與學習不相關的事例,會對一個孩子的心理形成什么影響,或許難以詳述,但一個12歲的孩子已經能很敏感地分辨出周遭環境中有多少是尊重和善意,還有多少是輕視和壓抑。陳欽怡說自己在公立學校上學的日子并不快樂,這種不快樂的感覺不是絕對的,也并不強烈,“因為學校里還有很多朋友”,但從機構層面,她感受到的溫暖和尊重很少。她的不快樂是孩子天性和自我意識被壓迫卻又無力反抗的不甘和無奈,這種并不明顯,但卻持續存在的低落情緒,只有接受了與傳統教育不同觀念的成年人才能覺察。
媽媽孫敏或多或少感受到了女兒這種情緒。當傳統學校還囿于體制進步緩慢時,很多家長已經在學著去體會孩子的感受,尋找更有效的和孩子溝通的方式。做母親后,孫敏也閱讀了很多有關教育孩子的書,并建立起自己對教育的取舍標準:“教育的根本是要立精神,人在天地之間,怎么能既適應社會,又找到自我。”她將自己思考的“好教育”評判標準歸結為幾條:“一是有利于孩子身體健康;二是幫助孩子建立自尊自信,以后到一個陌生環境中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三是情緒管理,能為負面情緒找到正確的出口;重要的是抗錯力,以后的世界瞬息多變,新問題層出不窮,孩子要有面對挫折的能力。”這是新一代家長的價值觀,大大超越以分數和知識為標準的傳統教育評判體系,需要一個不同以往的教育場所才能與之匹配。
尊重
在西方現代國家的教育史上,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現代教育發生變革的一個契機,促成兒童在教育中地位的重新思考和認識。兒童是什么?他應該以什么方式接受教育?這是貫穿西方近現代教育史的兩大問題。對西方現代教育影響深刻的是由杜威、蒙臺梭利等教育思想家在上世紀中期做出的探索和回答。雖然他們提出改革基礎教育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核心觀念都是一個——教育應該在尊重兒童的人格和天賦的基礎上進行。在此基礎上,一系列以兒童為教學中心的新式學校誕生,并逐漸星火燎原,成為西方學校教育中的普遍價值觀。選擇國際學校的家長關注的重點各不相同,但他們講述的故事中都包含著一個關鍵感受:尊重。
Funny回憶自己孩子上國際學校的經歷,有一個細節讓她至今還頗為感嘆。“有一次圣誕節,他們班要演一個舞臺劇,劇中的角色是各種動物,猴子、小豬、大象等等。我的孩子非常胖,所以我想他一定是演小豬。但結果并不是這樣,沒有讓他演小豬,也沒有讓班上非常瘦小的孩子演小猴。老師解釋這是對孩子的尊重,不能去強調丑化孩子的身材特點。他們為了尊重孩子,可以考慮到這么細致,這就是價值觀的不同。”
2014年,孫敏決定放棄這所眾人羨慕的公立學校,將女兒轉入一所外觀和設施上并不那么風光的國際學校。這所學校和另一所公立學校合用教室,甚至沒有獨立的操場,學生體育課要到校外租借的場地上課,但陳欽怡卻開始感覺到了上學的快樂。她感覺自己不再只是個俯首聽命的小孩,而是有獨立意識的學校的主人。學校的所有設施都可以使用,只需要刷學生卡,就可以使用學校的3D打印機完成作業,在圖書館任意翻看所有的書籍。這里鼓勵她發表自己的意見。與老師爭論問題,甚至是辨識優等生的一個重要標準。“我覺得自己更自信了,可以大膽跟人講自己的觀點,因為在學校每天都會跟老師討論發表意見,交往和表達的練習幾乎每時每刻都在進行。”作業留給孩子的操作空間也很大。近陳欽怡正在完成的是人文課作業——描繪一條河流。她選擇了歐洲的多瑙河作為模板,自己去網上搜羅了不少有關多瑙河的資料,然后畫設計圖,選擇河岸的風景和建筑,再用3D打印機把自己的設計變成現實,后還要為這條河流配樂。陳欽怡頗為享受這樣的過程,既認識更廣闊的世界,又可以加入自己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自己意識的主人。
國際學校通常是小班授課。Funny記得自己孩子上的國際學校,一個班只有12個人。“因為英聯邦的學校規定,一個班級的人數不能超過12個人,這樣保證老師有精力關注到每一個學生。”陳欽怡現在就讀的班級也只有十幾個人,整個年級的人數相當于原來公立學校的一個班。限定師生比,也是西式教育踐行“以兒童為中心”教育觀的細節體現。“學生沒那么多,感覺老師能關照到每個學生。”陳欽怡對本刊記者說,“每個孩子總是希望得到老師更多的注意。”
更多的關注對孩子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梅滿的故事可能更說明問題。上世紀90年代,梅滿媽媽從武漢來到北京,從事設計工作。經過十幾年的辛苦工作,她在北京城三環附近買了房子,建立起自己的家庭,但仍然沒有為自己和孩子獲得城市的居住憑證——戶口。“2002年孩子出生時,我們考慮過孩子以后可能會上私立學校。”梅滿媽媽回憶,“不過當時只是個隱約的想法,并不是家庭決定,因為覺得可能10年后,情況可能會改變。”
但12年后,有關城市居住權利和憑證的規定并沒有什么改變,如果孩子沒有北京戶口,進入公立學校有頗多限制,而且終無法參加北京市高考。對以高考為終指向的傳統教育系統來說,沒有北京戶口的孩子就讀公立學校是一條沒有出路的死胡同。因此在即將面臨初中的門檻時,梅滿媽媽也決定將孩子轉入一所國際學校。
在傳統學校就讀時,梅滿在老師眼中是個不太一樣的孩子。“老師曾經跟我說,覺得梅滿太天真,有很多幻想。”在傳統的評價標準里,這并不算一個值得稱道的特點,包含著與環境有些格格不入的含義。進入國際學校后,孩子愛幻想的特質卻得到了戲劇課老師的關注。她告訴梅滿媽媽:“小滿特別干凈、單純,他跟別的孩子不一樣。”梅滿媽媽聽到后,眼淚差點奪眶而出。每個孩子都希望被當成獨特的個體得到理解,每個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被當成獨特的個體獲得尊重。國際學校對每個孩子的個性提供了更多的關注和肯定,這套教育體系的迷人之處在于,它既給每個孩子留出了自我空間,又讓他感受到了被關注的存在感。
冒險
陳欽怡正在為明年初離開家去加拿大的一次培訓做準備。這是她12歲人生的一次冒險——一次獨自離開父母,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待3個月。她已經在盤算要一個人在外如何自我保護的問題:比如應該帶些什么物品,以備身體突然出現的不適狀況;如果與房東發生沖突,自己應該怎么據理力爭……
陳欽怡去加拿大是為了學語言。雖然她在公立學校讀書時英語不錯,而且課外堅持報班補習英文,但進入新學校后,仍然感覺到語言方面力不從心。國際學校是全英文授課,每個新入學的中國孩子的一個難關都是語言。梅滿從公立學校轉入國際學校后,一開始面臨的問題就是做作業的時間太長,常常寫到晚上十一二點,甚至到兩三點。“國際學校的作業與以前的作業有很大不同,更講究邏輯、格局,而且所有題目都是用英文描述。很多數學題其實很簡單,但描述題目的英文單詞對中國小孩來說太難,所以他常常在看懂題目上就要花不少時間。”梅滿媽媽說。
家長也同樣要遭遇陌生語言和課程的考驗。“在我們家里,姥姥姥爺先感到焦慮。”梅滿媽媽說,“他們突然完全幫不上忙了。”在大都市里,長輩參與是非常多白領家庭的育兒模式。在傳統學校就讀的幾年里,梅滿的姥姥姥爺是孩子日常學習的主要監護人,但轉入國際學校后,他們對輔導梅滿的功課就無能為力了。除了語言障礙外,還有思維的代溝。傳統課程里從來沒有的作業內容,比如描繪一條河流,或者設計一個城市,都讓老人們疑慮重重:孩子究竟能學到什么?
老人的擔憂,一方面來自無法理解新的教育內容,另一方面來自對這條陌生道路前景的不確定。全英文授課,開放式的教學方式,改變的不僅是孩子的上學體驗,也改變了整條教育路徑。選擇了國際學校的孩子,就很難再回到傳統教學的框架里——這意味著他們就此放棄中國高考,轉入一條“看上去很美”,但沿路卻有頗多斷裂的道路。
國際學校是把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模式鑲嵌到中國環境的一種教育模式。就像對外來物質的天然排斥反應一樣,這個嫁接進入的教育模式必然會和周圍環境表現出諸多的不適應。教師就是個例子。國際學校有相當部分教師來自國外,他們的素質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際學校的教學質量。但隨著北京的空氣質量越來越差,很多外籍人士都紛紛離開了這個城市。“可能會對教師的質量帶來影響,因為可供選擇的教師群體在減少。”梅滿媽媽說。
而在課程方面,不管教學方式有多么新穎有趣,但求學之路不可能永遠輕松。入讀國際學校的出路是進入國際高考的競賽場。對中國的孩子們來說,不管走在哪條路上,他們都逃不開族群的競爭。美國擁有全世界豐富、設備齊全的教育機構,這讓它的高考成為世界范圍的競爭平臺。美國的大學會傾向選擇不同族群中的較優者。也就是說,國際學生要進入好的高校,還是需要面臨和同族人的競爭。對中國學生來說,因為中國人的龐大基數,這條路的競爭同樣激烈。孫敏對此有清醒的認識:“IB課程(一類國際學校的教學課程)并不好學,越到后面越難,甚至超過中國高考的難度。進入高中后,課業負擔也會很重。”
因此,對選擇國際學校的普通家長來說,他們像是進入了一條通向更廣闊的未來,但卻更冒險的陌生路徑,家長們需要小心翼翼在前面幫孩子瞭望著這條路上的險情,提前為路上的溝壑鋪路架橋。對孩子來說,進入一個從語言到思維方式都完全陌生的教育體系也是一種需要付出心力的冒險,但路邊能看到不一樣風景的喜悅,會沖淡冒險的恐懼。就像陳欽怡所說:“我喜歡多嘗試一下不同的環境,因為那是我長大后也要去的地方。”
免責聲明: 1. 為方便家長更好的閱讀和理解,該頁面關于學校信息描述可能采用了學校視角,描述中涉及的“我”、“我們”、“我校”等第一人稱指代學校本身。并不代表遠播公司或其觀點;2. 此網頁內容目的在于提供信息參考,來源于網絡公開內容,具體以學校官方發布為主;3. 若素材有侵權或其他問題,請聯系我們:2787266480@qq.com。
預約看校
廣州市斐特思學校小學部 學校提供高品質的中英雙語教育,在全面覆蓋義務教育國家課程標準的前提下,深度融入國際項目的優秀元素,從而促進學習者成為中英雙語、全面發展、知識
廣州市斐特思學校初中部 初中部以國家課程標準體系作為堅實基礎,融合IB MYP框架,為課程內容增加了學術深度與拓展寬度,外教或雙語教師全英文或雙語授課占超70%,注重培養學生的
廣州市斐特思學校高中部 高中部為學生提供 IGCSE、A-Level課程,并提供雅思等語言考試培訓課程,讓學生無縫銜接進入世界名校深造。我校同時開設BTEC課程和劍橋藝術聯合書院,為9年級
南京赫賢學校 是一所放眼世界、融合中西、面向未來的高端民辦雙語學校,由義格教育集團傾力打造。以培養國際化的中國人為教育目標,為渴求國際化教育的中國家庭提供全方位、國
南師附校園Open Day 南師附校介紹 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學校秉承百年老校南師大的優良傳統,放眼世界、立足未來、服務家長,為人的成長創造最大的空間。 南師附校國際部2014年開辦
家長群大家除了討論學校YL各項事宜,還有一些家長關心部分民辦小學、初中能否住宿、費用等情況。我們匯總了今年南京民辦小學、初中學費、住宿情況以及招生范圍,供家長參考。
蘇州工業園區外國語學校 坐落在蘇州工業園區金雞湖東側,毗鄰奧體中心,是集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國際高中為一體的多語種外國語學校,面向中外籍學生同時招生,寄宿兼走
蘇州市相城區諾德學校 以創建一所真正的雙語學校為愿景,秉承諾德修身、安達立命的校訓,旨在培養充滿自信、德才兼備的雙語新生代,借助融合創新的雙語優質教育,助力學子圓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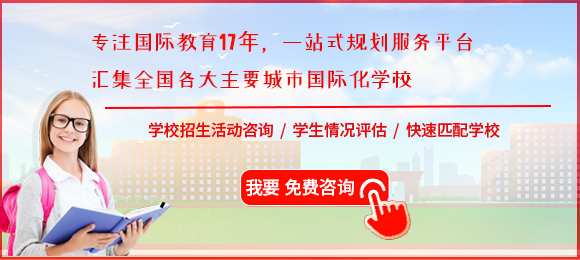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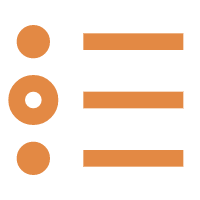 展會活動
展會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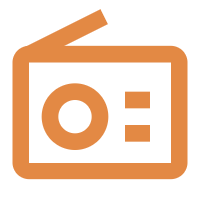 資訊熱推
資訊熱推





 周一到周日 08:00-21:00
周一到周日 0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