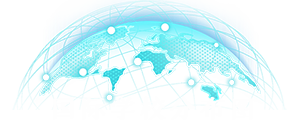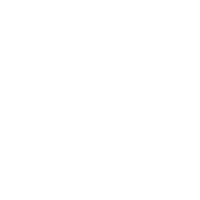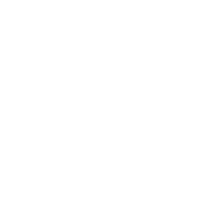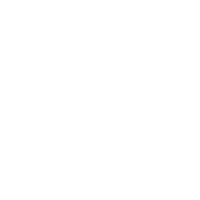一個窮苦孩子從國際學校走出閃亮人生路
時間:2017-07-11 14:07 國際學校網

武子璇在上海久牽志愿者服務社學會了彈鋼琴,并且會拉簡單的小提琴。澎湃新聞記者 賈茹 圖
武子璇跟隨做建筑工人的父親在工地的磚塊中間長大。2005年,離開老家江蘇沛縣后,她成了上海30多萬隨遷子女中的一員,在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上學。
而在開頭那段影像資料里,武子璇還是一支叫“放牛班的孩子”的合唱隊的成員,她的歌聲洪亮,對鋼琴也有特別的天賦。
當張軼超組建“放牛班的孩子”時,他受到一部法國電影的啟發——影片中,才華橫溢的音樂家克萊門特用音樂打開了一幫鄉村“問題少年”的心;在現實世界中,張軼超想通過音樂課程幫助隨遷的孩子們獲得一種美的熏陶。
40歲的張軼超是上海久牽志愿者服務社(下稱“久牽”)的創始人,從2001年起,這所機構為農民工隨遷子女提供公益教育服務。張軼超的另一個身份是上海一所國際學校的老師,教高中生TOK(知識理論)課,探討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在貧窮與富裕之間來回,張軼超試圖讓前者與后者一樣擁有多樣的選擇。
十一年里,一屆又一屆的“放牛班的孩子”長大:有人留在上海念中專畢業后進入社會;有人回到老家讀高中參加高考;還有8個人拿到了全額獎學金出國讀書。盡管許多人還在他們的命運軌跡里盤旋,但他們已經意識到自身擁有的可能性。
久牽
5月底的一天,下午五點多,張軼超出現在大學路上的久牽浦西活動中心。高而瘦的他戴著眼鏡,穿一套整齊的黑色西裝,內搭淺色襯衫,不扎領帶,看起來文質彬彬。
久牽浦西活動中心,張軼超在跟孩子們聊天。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
他隨意坐在彈鋼琴的凳子上,跟孩子們閑聊。鋼琴上放著一張十年前張軼超跟孩子們的合影,那時的他臉上還透著學生氣。
2001年,***哲學系研究生張軼超騎著自行車,穿過校區,由國權北路轉入廢棄的江灣機場,無意間闖入一片外來農民工聚居區,這里有幾所農民工子弟學校。
學校是在廢舊廠房的基礎上蓋的,孩子們灰頭土臉地在空地上跑,看到張軼超脖子上掛著相機,就一個個沖到他面前,擺各種姿勢,要他拍照。
張軼超組織***學生去學校支教,但課堂上很吵,有人打鬧,有人寫作業,有人擤鼻涕,還有人在吃東西,只有很少的人在聽課。學校的老師,對志愿者也愛理不理,甚至對志愿者糾正孩子們的英語發音不滿。
一次,他的一個朋友來學校,帶了許多文具和一大袋糖果。張軼超把糖果交給校長分發,可當他走出在二樓的校長辦公室,只聽到身后傳來興奮的喊聲:“孩子們,快來吃糖啦!”他轉身一看,糖果在空中飛,孩子們拼命地爭搶,有人打起來,有人哭起來。。。。。。這個畫面讓張軼超無法釋懷。
他在想,這些孩子的未來會是怎樣的呢,“他們需要的是較優的老師和系統的教育,而非物質上的暫時改善。”
張軼超打算開辟新的教學場所,他在國權北路上租了一套房子,作為教學點。“久牽”誕生了。
從2002年2月開始,除了語文、數學、英語等主課是志愿者到農民工子弟學校教授,其他所有興趣類課程,都在“久牽”進行,這些課程包括天文、音樂、繪畫、電腦、歷史、詩歌、攝影等,張軼超想讓孩子們了解更多有趣的事情。
端午節,久牽浦西活動中心,孩子們在學習制作粽子。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
岔路口
據2007年上海市教育事業統計,截至2007年9月,上海接受義務教育的外來流動人口子女近38萬人,其中初中階段8萬多人。
新華網2008年的一則報道援引共青團上海市委、上海市社區青少年事務辦的調查稱,初中畢業后,有約一半來上海農民工子女留滬跟隨父母一起經商、幫工,或進入成人中專、技校或其他中等學校就讀,另有一半來滬務工人員子女散落在社會之中,處于就學就業兩難境地。
姚如惠是久牽的孩子中一批站在“岔路口”的人。1992年出生的她,在7歲時跟隨父母從老家安徽蚌埠來到上海。2006年,父母要把讀初一的她送回老家——姚如惠的父親因家境貧寒,讀完初中便輟學,一直心懷大學夢,認為考大學才有出路。
對于隨遷子女來說,從小離家,他們對家鄉的記憶非常模糊,老家通常只是身份證上的一串地址,只有在需要填寫住址信息時,才會翻出來查看。而因為教材版本、教育環境和上海也很不一樣,他們回家后通常要經歷一段艱難的適應期。
姚如惠去了一個寄宿制學校,班上90多個學生,每天六點早自習,九點晚自習結束。她成績優異,中考進入縣城一中好的 “火箭班”,但這里課業壓力很大,下課后,所有人都在看教輔資料做題目。一次她數學測試考了108分(滿分150分),被老師點名批評,直到她下一次考了130多分,才提心吊膽地躲過點名。
姚如惠在那里像完全變了一個人,不怎么跟同學講話,整天擔心成績跟不上。她很困惑,為什么要回到老家,她也不知道是否應該回上海。
當姚如惠在高考的題海里奮戰時,升入初中的林蘭蘭,也面臨去和留的選擇。
1995年生的林蘭蘭是河南周口人。2000年,父母把她和比她大兩歲的姐姐林慶慶,比她小兩歲的弟弟林創創都帶到了上海。
爸爸初的工作是收廢品,媽媽是保潔員。白天他們上班,怕孩子受欺負,就把他們鎖在家里。對面一戶人家有兩個兒子,把沙子石頭扔到林蘭蘭家鍋里,三個孩子氣得不行。等到父母回家,門一開,林慶慶就沖出去揍對面的男生。
姐姐林慶慶讀完小學,被父母送到老家的寄宿學校。班上有130多個學生,60個人住一間宿舍,睡上下鋪。她不僅無法適應那里的教育方式,還水土不服,渾身長痘,得了慢性胃炎,一年后,林慶慶又回到上海。
林蘭蘭成績較優,小學初中都是班長,父母也希望她可以回家考大學。但林蘭蘭不想回去,她還是喜歡上海。
合唱團
2006年,一個跟平常無異的早晨,林蘭蘭穿著松垮的秋衣,滿身塵土地站在學校的操場上做完早操,在校長發表枯燥的講話后,一個年輕的男人突然走上臺對他們說,想組建一個合唱團。
他就是張軼超,在宣布組建合唱團的消息后,同行的志愿者柯慧捷拿出吉他彈奏起來。從沒見過吉他的孩子們,臉上寫滿了新奇,都跑過去想要摸吉他,新奇感跟“這個合唱隊肯定很好”畫上了等號。
幾百個學生排起長隊報名,一個個試音,終篩選出36個人。林蘭蘭、林慶慶都被選上了。
多年后,張軼超回憶,組合唱團其實是件“拍腦袋”的事兒。一天晚上,他看了法國電影《放牛班的春天》,看完后就有點小興奮,“哎,辦個合唱團挺好。”
他給合唱團取名“放牛班的孩子”。每周上兩次課,孩子們從發音開始學,張軼超托著腮幫子坐在一旁聽,“盡管他們很吵,唱得也不咋地,但很投入很認真”。
久牽浦西活動中心,鋼琴上放著十年前“放牛班的孩子”合照。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
一開始,他也聽得頭大——這畢竟是一群從沒上過音樂課的孩子,張軼超那時心想,怎么唱成這個樣子。但兩個月后,孩子們越唱越好,聽他們排練,變成一種享受。
在張軼超看來,合唱團也許不會改變人生,但會讓人生更豐滿一些。
隨遷子女的父母幾乎都是全年無休地工作,沒空陪伴孩子,彼此之間也缺少交流,許多孩子寡言少語,不愿表達,如果父母老師責怪他們,他們尋常的態度就是沉默。
玩是張軼超跟孩子們建立信任的方式。新江灣城曾是一塊濕地,張軼超帶著孩子們去那里抓蟲子,鼓勵他們帶回去養。他還帶他們玩藏寶游戲,打羽毛球,抓龍蝦,放風箏,探險,看電影,打游戲。。。。。。
孩子很容易厭倦,他需要不斷開發新鮮玩意兒。他拿著天文望遠鏡帶他們去看星星,帶他們到外灘拍攝汽車的尾燈、前燈,教他們如何曝光,拍出漂亮的光帶。在姚如惠的印象中,她跟著張軼超走了很多很多路,每天走得腳疼,“我們去江灣鎮靠走路,來回要走七八公里。”
他帶他們去吃沙縣小吃,肯德基和高檔食物。有些孩子吃了高檔食物,會跟別人說:哎你知道嗎?我今天吃的這個東西多少多少錢。
張軼超會教育他們:“我帶你吃這些東西不是想讓你跟別的小孩炫耀,在我看來,不管是沙縣小吃還是幾百塊的菜,沒有任何區別,我只是想讓你體會這個世界的豐富性,食物可以做成這樣,也可以做成那樣。”
就在這些細微小事的指點中,孩子們開始認識世界,獨立思考。
2006年,合唱團在上海電視臺參加演出,演出結束后,歌迷把熒光棒扔在舞臺上,十歲左右的孩子們一窩蜂沖上舞臺搶熒光棒。
張軼超很生氣,把他們訓了一頓,“搶得臉紅脖子粗,我讓他們去想,為什么要去爭搶這些熒光棒?”
站在回鄉與否的人生岔路口,久牽的孩子們也需要去想很多“為什么”。
在大多數隨遷子女的父母看來,回鄉參加高考是唯一“出息”的可能,但林蘭蘭沒有回鄉,她在上海讀了中專。基于自我的認識,對自己的人生做出選擇。這是張軼超在國際學校上的知識理論課的內容,他希望久牽的孩子也能認識和創造更多的可能。
出路
2009年的一天,張軼超從朋友處得知,有一個國際學校,可以提供免費的全額獎學金,前提是學生足夠較優。
這個學校就是UWC(世界聯合學院),它成立于1962年,吸收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張軼超希望久牽的孩子去試一試,后來王新月、姚如惠和劉燕霞三個同齡的女孩被送到北京免費學托福。
那時正是姚如惠高考前幾個月,她請了一個月假學托福。班主任覺得她在“瞎搞”,父母也強烈反對。申請UWC時需要班主任寫推薦信,但班主任說,這學校是騙子,“看名字大可能是騙子”。
在張軼超的建議下,姚如惠還報考了***的自主招生,但“題目超難”,她考得很差;她還嘗試直接申請去國外讀大學,也失敗了。后階段,姚如惠突然就氣餒了,給UWC的申請書寫了,卻沒有寄出去。
不夠堅定的劉燕霞也沒有投遞申請書。
劉燕霞是重慶人,跟著父母到上海后換了三個小學,初中時,她進了唐鎮中學。唐鎮中學不僅有上海本地學生,也有外地學生,初一時按成績分班,劉燕霞成績年級一,在一班。初二時,考慮到外地學生不能參加中考,學校按戶籍分班,劉燕霞就被劃到二班。
整個初中三年,劉燕霞的成績一直保持在年級一,她還參加各種課外活動,比如每周去高橋烈士陵園做講解員。“那時候特別不理解,我為什么不能上高中,比我成績差的都能上。”
初一剛結束,劉燕霞考察了老家的學校,發現不僅教材版本不同,學習環境也完全不一樣。“唐鎮有征文活動,但他們只有上課、考試,不能看課外書,我很失望,還是想回來。”
三人中,只有王新月一人終投遞了申請書。2011年1月,她收到了面試通知,張軼超陪她去北京參加面試。
UWC喜歡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學生,王新月跟他們討論,如果她是政府工作人員,想做哪些事情。在回來的出租車上,張軼超對她說:“你很關鍵啊,王新月,你肩負著很多人的命運呢。”
2011年4月,王新月被UWC錄取了。她的成功讓久牽其他孩子看到了希望,申請UWC一時在久牽成為“風潮”——但UWC官網上顯示,他們的總錄取率只有5%。
林蘭蘭原本對自己未來的設想是:讀完中專先工作,邊工作邊考夜大。她認為做什么工作沒太大關系,只要努力,保持向上的生活狀態,就可以在上海站穩腳跟。
在中專一年級時,林蘭蘭首次申請UWC被拒。后來,一個去了UWC的學生回到久牽,分享在國外的學習經歷,林蘭蘭托著腮,滿眼的羨慕:“那你就講一件,在UWC好玩的事情吧。”
2014年這一年,久牽有三個孩子被UWC錄取,分別去香港、英國、德國讀大學兩年預科。林蘭蘭是其中的一個,這是她的二次申請,她去了英國。
選擇
在王新月被錄取這年,姚如惠也考上了安徽大學。
進入大學后,她感到有些迷茫,一個月就萌生了退學的想法。姚如惠去找張軼超,張軼超告訴她:“你要退學也沒有太大問題,但你前面的努力……你退學之后干什么呢?沒有想清楚就不要退。”
同齡的劉燕霞這一年進入上海信息技術學校讀中專。中專畢業后,劉燕霞經過層層面試,找到一份跟專業對口的公司實習。
那家公司很大,劉燕霞喜歡公司自由的企業文化,那段時間,她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轉正。
但那個寒冷的冬天,她被告知沒有被錄用,她在租的房子里痛哭不已,“我也知道文憑很重要,有時也會感覺到跟室友的差距,一想到自己的未來,真的會哭。”
2008年,張軼超在浦東建了二個久牽活動中心,劉燕霞是唯一一個浦東合唱團成員。下午4點半放學,她跟著張軼超一起,換乘好幾趟公交,從浦東坐將近兩個小時車去浦西排練。
讓她印象深刻的是,大家都把久牽當家一樣。一開始,浦西的孩子不知道她的名字,就喊她“浦東的、浦東的!”
每周一次的合唱讓劉燕霞很期待,“老師會教我們用氣息唱歌,五線譜怎么看,拍子怎么打。”除了唱歌,劉燕霞還在這里學英語,上興趣課。
小時候,她曾有很多個夢想。等到長大了,有的忘了,有的沒有實現。“接觸到合唱我就想當合唱老師,接觸記者想去做記者。張老師鼓勵我,說這是孩子的天性。”
多年后,劉燕霞向記者回憶這些往事時,還會陷入更久遠的記憶:
2000年,她跟隨父母,沿長江坐船到上海。全家人搬了一箱子泡面,在船上吃了一個禮拜。爸爸初在上海做門衛,一家三口就擠在浦東唐鎮的一間門衛室里住。
在上海生活了17年,劉燕霞看著周圍的摩天大樓,常覺得自己不屬于上海,走到哪里都在漂泊。
畢業后,她獨自在外租房,有時跟父母匆匆見一面,他們叮囑她好好工作掙錢。“給你養大了,成人了,下面的路就由你自己走了。”
實習沒有通過,久牽的一位老師推薦劉燕霞去了一家蛋糕店。她在那里負責包裝蛋糕,但沒多久,她就辭職了。劉燕霞覺得那份工作沒有價值,輾轉又換了兩份工作,一直在尋找自己真正想做的。
回到久牽
2015年,姚如惠大學畢業,回到了久牽。她目標清晰,張軼超曾經帶她走過的路,她想循跡前行,如今她是久牽浦西活動中心負責人。
久牽浦西活動中心負責人姚如惠在接待志愿者。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
久牽浦西活動中心位于***附近的大學路,一百來平方米的屋子里鋪著地毯,四周擺著鋼琴、吉他、電腦,書柜里有各種書籍,架子上擺滿了玩具、桌游……
下午三點多,風從陽臺上吹進來,林慶慶在客廳鋪上瑜伽墊慵懶地躺下,有人在彈吉他,有女生隨著吉他聲唱起歌來。
過去十年,久牽每年接受的孩子大約100人,不斷有人離開和加入。某種程度上,久牽就像他們的避風港。林蘭蘭回國有時就住這里,林慶慶生活不順時會逃來這里,屠文建中專畢業工作不如意時也是回到久牽。
1994年出生的屠文建是安徽霍邱人,5歲來滬,2006年,他成為“放牛班的孩子”的一員。屠文建癡迷于唱歌,小時候夢想當歌星,在合唱隊時他當領唱,“覺得我很牛逼!”
小學畢業后,屠文建不愿意回老家,他在上海讀了中專,但不喜歡學的計算機專業。跟林蘭蘭一樣,屠文建也曾申請UWC,但只申請到半額獎學金,就沒去。
2013年,離畢業還有一年,他已經修滿學分,想早點出來掙錢,經張軼超推薦,他去了一家工廠。原本想去學財務,但去了之后,工廠安排他去流水線。
他的工作是在流水線上修機器,早中晚三班倒。“那班人都比我大,他們想的東西跟我想的不一樣。他們都是想賺錢,我是想學東西,但是學不到東西。還要跟領導撒謊,討好師父,不然待不下去。”屠文建難以融入到工廠生活中。
他不喜歡這個工作,但在學校沒有事做,也找不到別的工作。這里每天加班,一個月可以拿到6000多元,他用“熬時間”形容自己那時的狀態,壓抑的時候就拿拳頭對著墻壁打。
兩年后,屠文建辭職,回到久牽做會計,一個月工資3500元,但他不介意比工廠低。“這是我的家,我在家里工作,拿3500,已經很開心了。”
林慶慶現在在一家教育公益機構工作,每天要陪伴孩子們完成課后作業。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
屠文建現在一邊工作,一邊自考大專,他想繼續讀大學,也想一直留在久牽,這里讓他有安全感。但母親馬紹玲并不滿意兒子現在的工作,因為工資不高。
他們家靠近寶山江灣鎮,是個由倉庫改成的房屋,一家住在二樓的一個十幾平方米的房間里,一個月租金1100元。家里很簡陋,一張雙人床,一張上下鋪,下鋪是屠文建的床,上鋪堆滿了雜物。
屠文建(左一)和媽媽弟弟在出租房里。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
馬紹玲寄希望兒子通過讀書改變命運,但屠文建成績不夠好,來到上海后,她又生了個兒子,也在久牽,現在讀小學,她打算明年帶他回老家讀書。
“你有想過找別的工作嗎?”記者問屠文建。“no!那樣的人際關系不適合我。在別的地方沒有在這里自由。”
命運軌跡
在上海生活七年之后,2012年,讀初二的武子璇跟著母親回到了戶籍所在地,江蘇沛縣。
她還記得幾年前,離開老家的那晚是深夜,母親把她叫醒,弟弟在母親的懷里酣睡,而她困得睜不開眼,拽著母親的衣服閉著眼睛往前走。
武子璇在老家讀完了初中,高中。2017年6月,她參加了自己的二次高考,她希望高考后,去外面看看,把握自己未來的路。
劉燕霞如今在張軼超所在的學校做實驗員,有一個干凈獨立的辦公場所,她很喜歡這份工作,希望有一天可以當學科老師。2015年12月,她自考拿到大專學歷,現在自考本科,還剩下三門課畢業。
劉燕霞在實驗室里工作。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
受張軼超影響,林慶慶和另一位久牽的孩子侯學琴畢業后都選擇做公益。五月底,侯學琴辭去自己畢業后的二份工作,進入一家關于水污染的公益機構工作。“工資不是很高,但是做得開心就好。”
而王新月和弟弟王澤方、妹妹王雪蒙都考上了UWC。
從UWC畢業后,林蘭蘭申請到美國一所大學的全額獎學金,已經讀完大一。今年5月,40歲的張軼超結婚,林蘭蘭回來參加婚禮。不久后,她又匆匆前往墨西哥參加夏令營,學習西班牙語。
2014年,張軼超給林蘭蘭等四個“放牛班的孩子”頒發了久牽的畢業證書,上面寫著:“感謝你在久牽這個家付出的努力與勇氣!祝賀你已經擁有自由的靈魂。”
林蘭蘭從張軼超手里領到畢業證時覺得,好像要永遠離開久牽這個大家庭,未來的路會越走越遠。
久牽的孩子們來來去去,但張軼超像大樹一樣扎在那里。2002年他碩士畢業,公立學校那時待遇好,但他去了私立學校,在學校上課外的時間,都用來陪久牽的孩子。
有時別人會問他的父母,你兒子復旦畢業啦,去哪兒啦?在做什么呢?父母感覺受到打擊,不知道怎么回答。
張軼超為此曾和父母發生爭吵,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如今,盡管久牽多次被媒體報道,受到贊譽,但張軼超仍然無法讓父母為他做的事情而自豪。“他們會覺得上個電視被采訪不是了不起的事情,能拿高薪才是。”
久牽的TOK課上,張軼超在給孩子們上課。 澎湃新聞記者 張維 圖
5月27日,張軼超在久牽給孩子們上TOK課,他提出一個問題:成功是什么?
八個學生圍著他,大的23歲,小的在讀初三。初三的男孩王振濤不假思索地回答:“久牽就很成功啊,他改變了我們外地孩子的命運。”
張軼超望著他,微笑著說:“我們還沒有成功。”
在他看來,成功是突破自己既有的限制,也可以稱之為命運。比如,流動兒童的命運通常是,初中畢業以后讀個中專或者學個技術,成為普普通通的技術工人,或者做點小生意,成為個體戶。在這樣的命運里,他們很少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價值,更多是為了謀生。“我覺得他只是意識到自身擁有很多可能性,但他依然還在他的命運軌跡里,沒有跳出來,他未來還要面臨很多束縛和壓力。”
從久牽走出去的孩子,有人去了UWC,有人考上了大學,還有的人中專畢業。無論哪條路這些孩子都面臨需要突破的命運。
“去UWC的孩子,只是進入了另外一個命運軌道,他們在國外讀完大學之后,也會有一條既定的道路,進外企,在寫字樓里面工作等等,這又是一個他們要突破的內容。”但張軼超覺得,可以獨立地認識這個世界,然后有勇氣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們在久牽就畢業了。
免責聲明: 1. 為方便家長更好的閱讀和理解,該頁面關于學校信息描述可能采用了學校視角,描述中涉及的“我”、“我們”、“我校”等第一人稱指代學校本身。并不代表遠播公司或其觀點;2. 此網頁內容目的在于提供信息參考,來源于網絡公開內容,具體以學校官方發布為主;3. 若素材有侵權或其他問題,請聯系我們:2787266480@qq.com。
預約看校
佛山市霍利斯外籍人員子女學校 (佛山霍利斯)是一所走讀及寄宿學校,為學生們提供卓越的英國國際課程。歡迎6至18歲的學生報讀。我們將英國寄宿學校帶到佛山,一座位于粵港澳大灣
校園簡介 上海閔行區諾德安達雙語學校坐落于 上海市閔行區,于2016年9月建校,是一 所融中西文化精粹、推進雙語教學的十 二年一貫制學校。旨在為年齡在6歲至 18歲的學生建立一所富
雙威國際學校介紹 雙威教育集團(Sunway Education Group)由謝富年基金會持有并管理,旗下院校包括雙威大學、雙威學院、莫納斯大學雙威院校、雙威國際學校、謝富年醫學與健康科學院等共
從兩千多年前的古巴比倫空中花園到瞬息萬變的現代城市,人類從未停止對工具與自然的探索。我們當下生活在一個祛魅的時代,科學與理性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占據了愈發重要的地位
從兩千多年前的古巴比倫空中花園到瞬息萬變的現代城市,人類從未停止對工具與自然的探索。我們當下生活在一個祛魅的時代,科學與理性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占據了愈發重要的地位
在古老的頤和園西,美麗的香山腳下,玉泉山邊,坐落著一所書聲瑯瑯、生機盎然的學校,這就是年輕的北京市師達中學。學校創辦于2001年,目前在校生2000人,共45個教學班。學校校風
隨著上海國際學校春招落下帷幕,同學們也開啟了寒假生活。前段時間,領科率先發布了2025秋招情況,七德、WLSA學校也陸續跟上。 隨后又有部分學校公布了秋招信息,今天我們就趁著
上海高藤致遠創新學校 創辦于2017年,是與綠地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全球500強企業綠地集團控股子公司)戰略合作開設的創新型國際課程學校。學校配有現代化的日常教室、多功能教室、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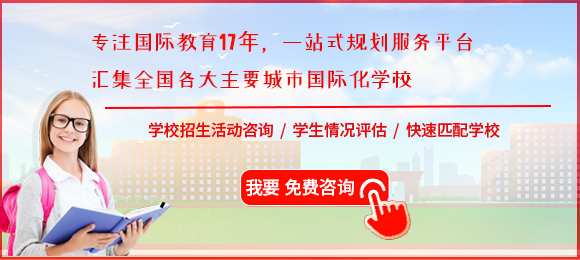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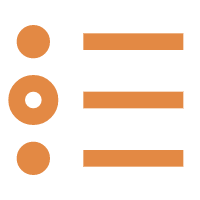 展會活動
展會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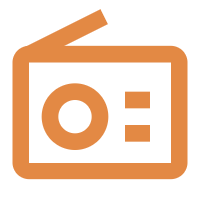 資訊熱推
資訊熱推





 周一到周日 08:00-21:00
周一到周日 08:00-21:00